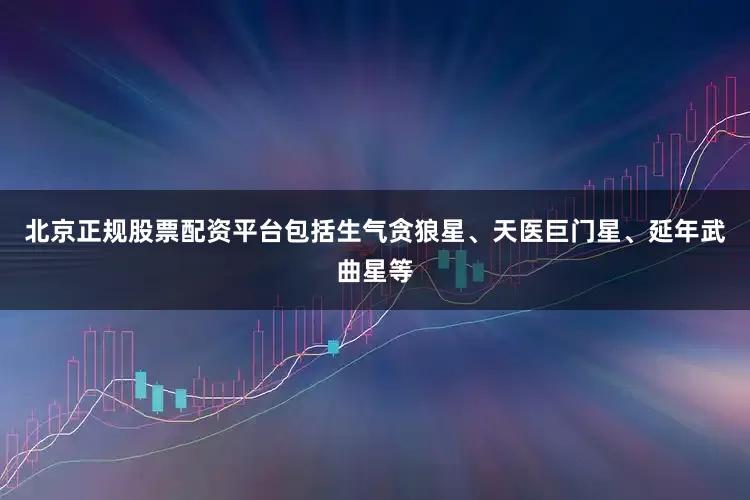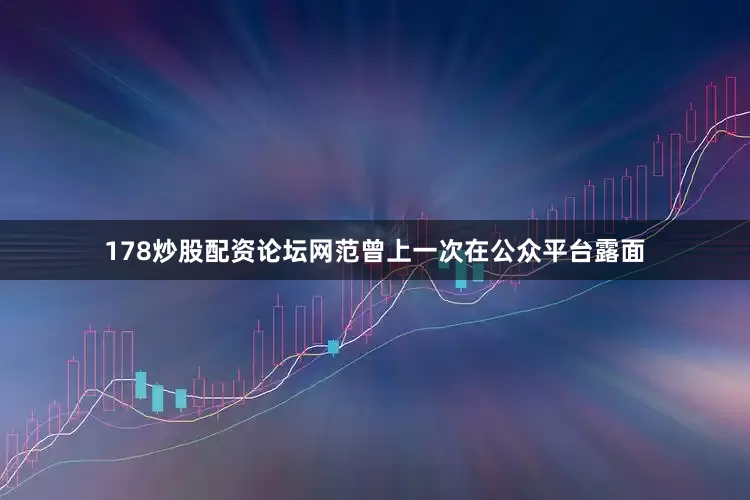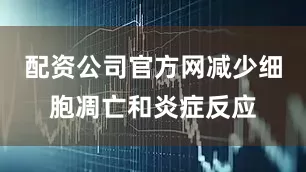那年冬天,家里断粮了。
父亲让我带着五岁的弟弟去大姨家借5斤面粉。
"记住,就说家里暂时困难,过两天就还。"父亲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我牵着弟弟的手,背着空布袋,踏着雪花走了十几里山路。
大姨家很冷淡,大姨夫更是不太愿意借给我们。
最后大姨还是给了我们5斤面粉,但态度很平淡。
回到家,我把沉甸甸的布袋递给父亲。
父亲接过袋子,打开一看,瞬间瘫坐在地上,泪如雨下。
"这...这怎么能要..."父亲颤抖着声音说道。
我不明白,大姨到底在面粉袋里放了什么,能让从不掉眼泪的父亲如此失态...
展开剩余96%01
198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,十月底就下了第一场雪。我叫李建国,那年我十三岁,弟弟李建军才五岁。
那时候的东北农村,冬天格外漫长寒冷。我们家住在黑龙江省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,父亲李大山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,母亲在我八岁那年因病去世了,留下父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兄弟俩。
这几天家里的情况特别糟糕。
"爸,我饿。"小建军拉着父亲的衣角,眼巴巴地看着他。
父亲蹲下身子,摸摸弟弟的小脑袋:"乖,爸这就去想办法。"
我站在一旁,看着父亲眼中的无奈和心酸。家里的粮食早在半个月前就吃完了,这些天我们都是靠着邻居王大娘偶尔送来的剩菜剩饭度日。
昨天晚上,父亲又咳了一整夜,我听到他在被窝里压抑着咳嗽声,生怕吵醒我们。早上起来,我看到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,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
"爸,您的咳嗽又厉害了。"我担心地说。
"没事,没事,就是着了点凉。"父亲摆摆手,但我注意到他说话时气息有些不稳。
父亲是个要强的人,从来不愿意主动向别人开口借东西。但现在,两个孩子饿着肚子,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我看到父亲在房间里来回踱步,脸上的表情很纠结。他时而看看我们,时而又叹气,显然在做什么艰难的决定。
"建国,你过来。"父亲终于下定决心,把我叫到一边,压低声音说:"你带着建军去你大姨家一趟,借5斤面粉回来。"
我点点头。大姨李秀华是父亲的亲妹妹,嫁到了县城里,丈夫在供销社工作,日子比我们过得好一些。但是,我记得上次见到大姨还是在三年前,她来给母亲上坟的时候。
"大姨会借给我们吗?"我有些不确定地问。
父亲犹豫了一下:"应该会吧,毕竟是一家人。"
但我从父亲的语气里听出了不确定。其实我们和大姨家的关系并不算特别亲近,母亲去世后,两家的联系就更少了。
"记住,就说家里暂时困难,过两天秋收的粮食卖了就还。"父亲的声音有些颤抖,显然开这个口对他来说很不容易。
"爸,我知道怎么说。"我懂事地点头。
父亲从床底下翻出一个洗得发白的布袋,检查了一下,确认没有破洞后递给我:"拿着这个,路上小心点,照顾好建军。"
我接过布袋,感觉它很轻,但责任却很重。
"爸,如果大姨不借给我们怎么办?"我忍不住问出了心里的担忧。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"那就...那就再想其他办法吧。"
我知道父亲其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,这已经是最后的选择。
我背上布袋,牵起弟弟的手。弟弟穿着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棉袄,小脸冻得通红。
"哥哥,我们要去哪里呀?"弟弟仰着头问我。
"去大姨家。"我简单地回答。
"大姨是谁呀?我不记得了。"弟弟眨着大眼睛。
"是爸爸的妹妹,你小时候见过的。"我解释道。
"她会给我们好吃的吗?"弟弟天真地问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只能说:"我们去了就知道了。"
父亲送我们到门口,看着我们的背影,眼圈有些发红。我回头看到他站在门口,那个瘦削的身影在雪花中显得格外孤单。
"爸爸,我们会很快回来的!"我大声喊道。
父亲点点头,挥挥手,然后转身回了屋里。
02
从我们村到县城要走十几里山路,平时大人走也得两个多小时,更别说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了。
雪越下越大,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。我牵着弟弟的手,小心翼翼地走着,生怕他滑倒。
"哥哥,雪好大呀。"弟弟伸出小手接雪花,很兴奋的样子。
"是啊,但是我们要快点走,不然天黑了就找不到路了。"我催促他。
走了一个小时,弟弟就开始喊累:"哥哥,我走不动了。"
我蹲下身子:"来,哥哥背你一会儿。"
弟弟趴在我背上,小手紧紧搂着我的脖子。虽然他很轻,但对于十三岁的我来说,背着他走山路还是很累的。
"哥哥,你累不累?"弟弟在我背上轻声问道。
"不累。"我撒了个善意的谎言。
"哥哥,爸爸为什么总是不开心呀?"弟弟又问。
这个问题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不能告诉一个五岁的孩子,我们家穷得连饭都吃不起,我也不能说爸爸生病了却没钱看医生。
"爸爸想妈妈了。"我只能这样回答。
"我也想妈妈,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?"弟弟的声音里带着期待。
我心里一酸,弟弟太小了,还不明白生死的概念。我曾经无数次想要告诉他真相,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"妈妈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,等我们长大了,她就回来了。"我只能这样哄他。
走了一半路程,我们在路边的一个小亭子里休息。弟弟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饼干,那是昨天王大娘给他的。
哥哥,你吃。"弟弟把饼干递给我。
"你吃吧,哥哥不饿。"我推辞道。
"可是哥哥肚子在叫呢。"弟弟认真地说。
我确实很饿,但我不能吃弟弟仅有的一点食物。
"哥哥刚才吃过了,你快吃吧。"我继续撒谎。
弟弟将信将疑地把饼干吃了,但他很聪明,只吃了一半,把剩下的又包好放进口袋里。
"留着路上饿了再吃。"他说。
看着弟弟懂事的样子,我鼻子有些酸。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节约食物,知道为以后考虑,这本不应该是他这个年龄该承受的。
休息了十分钟,我们继续上路。雪越下越大,路也越来越滑。我背着弟弟,一步一步地往前走,每一步都很小心。
"哥哥,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呀?"弟弟问。
"快了,再走一会儿就到了。"我安慰他,虽然我自己也不确定还要走多久。
又过了一个小时,我们终于看到了县城的轮廓。那些砖瓦房屋在雪花中若隐若现,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希望的灯塔。
"哥哥,那里就是县城吗?好多房子呀!"弟弟兴奋地说。
"是啊,大姨就住在那里。"我也松了一口气。
进了县城,我们按照记忆中的地址寻找大姨家。县城虽然不大,但对我们这两个农村孩子来说,还是很容易迷路的。
我们在街上转了半个小时,问了好几个人,终于找到了大姨家的地址。
那是一个四合院的一角,一间不算大的房子,但比我们家的泥草房强多了。房子是砖瓦结构,门前还铺着几块青砖。
我站在门前犹豫了一会儿,心里有些紧张。我们这样突然上门,大姨会不会觉得我们是来打秋风的?
"哥哥,我们不进去吗?"弟弟仰头问我。
"进,当然进。"我深吸一口气,敲了敲门。
03
"谁呀?"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,但语调听起来有些警惕。
"大姨,是我,建国。"我紧张地回答。
门内传来脚步声,然后门开了。大姨李秀华出现在门口,她比我记忆中的样子老了一些,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,脸上的表情很平淡。
"建国?"大姨看着我,似乎在努力回忆,"你怎么来了?"
她的语气不算热情,也不算冷淡,就是很平常的那种语调,让我有些摸不透她的想法。
"大姨,这是建军。"我拉着弟弟往前一步。
大姨低头看了看弟弟,点点头:"长这么大了。进来吧,外面冷。"
我们跟着大姨进了屋里。屋子不算大,但很整洁,炉子烧得不是很旺,屋里的温度刚好不冷。墙上贴着一些年画,桌子上放着几个苹果,但看起来有些蔫。
"坐吧。"大姨指了指炕沿,然后给我们倒了两杯温水。
水不算热,温温的,但对冻了一路的我们来说已经很好了。
"你们怎么想起来看大姨了?路这么远。"大姨坐在我们对面,语气依然很平淡。
我握着水杯,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原本想好的话,到了嘴边却说不出来。
这时候,大姨夫王建华从里屋走了出来。他是个中等身材的男人,穿着中山装,看起来挺精神,但脸上的表情比大姨还要冷淡。
"这是哪家的孩子?"王建华问大姨,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。
"我哥家的,建国和建军。"大姨简单介绍。
王建华"哦"了一声,看了我们一眼,然后说:"怎么这时候来了?外面下这么大雪。"
他的语气让我感觉有些不舒服,好像我们的到来很不合时宜。
"他们可能是有什么事。"大姨说,然后看着我,"建国,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?"
我感觉到大姨夫在旁边看着我们,眼神不太友善。我深吸一口气,决定直接说出来。
"大姨,我们家...家里暂时有些困难,想借5斤面粉。"我低着头说,脸红得像苹果。
说完这句话,屋里突然安静了下来。我能感觉到大姨和大姨夫在交换眼神。
"借面粉?"王建华的声音里明显带着不高兴,"你们家大山怎么了?"
"没...没什么大事,就是暂时困难,过两天就还上。"我赶紧解释。
王建华皱了皱眉:"暂时困难?困难到连5斤面粉都没有?"
他的话让我很难堪,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大姨看了看王建华,又看了看我们,脸上的表情很复杂。
建华,你先别说了。"大姨对丈夫说,然后转向我们,"建国,你爸爸现在在干什么?身体怎么样?"
"爸爸在家里,身体...还行。"我不敢说爸爸一直在咳嗽,怕他们更加不愿意帮助我们。
"还行?"王建华冷笑一声,"要是身体好,怎么会连5斤面粉都弄不到?"
他的话很刺耳,让我感觉很屈辱。但为了完成父亲交给我的任务,我只能忍着。
"建华,你别这样说话。"大姨又制止了丈夫,但语气也不是很坚决。
王建华走到窗边,背对着我们:"秀华,我们家的日子也不宽裕,供销社的工资就那么点,还要养活一家人。现在外面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城里工作,三天两头有人来借东西,这样下去可不行。"
他的话虽然不是直接对我们说的,但意思很明显:不想借给我们。
大姨脸上的表情更加为难了。她看看我们,又看看丈夫,似乎在做什么艰难的决定。
"大姨,如果不方便的话,我们就不借了。"我看出了她的为难,准备起身告辞。
"别急。"大姨按住我的胳膊,"坐下,让大姨想想。"
屋里又是一阵沉默。弟弟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,紧紧抓着我的衣角,一声不吭。
04
这种沉默持续了好几分钟,让我感觉如坐针毡。
王建华转过身来,脸上的表情依然不好看:"秀华,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但是我话说在前头,这种事情不能开先例,否则以后会有更多人来借东西。"
说完,他就进了里屋,临走时还重重地关了一下门。
大姨尴尬地笑了笑:"建华他就是这个脾气,你们别往心里去。"
但我能看出来,她自己也很为难。
"大姨,要不我们回去吧。"我再次准备离开。
"别,你们大老远来一趟,怎么能空手回去。"大姨站起身,"你们先坐着,我去准备一下。"
她走向里屋,我听到她和王建华在低声说话,但听不清内容,只能听出王建华的语气很不耐烦。
过了一会儿,大姨从里屋出来,手里拿着一个布袋。
"建国,把你的袋子给大姨。"她说。
我赶紧把父亲给我的布袋递过去。大姨接过袋子,检查了一下,然后说:"你们在这里等一下,大姨去给你们装面粉。"
她拿着袋子走向厨房。我听到里面传来舀面粉的声音,还有大姨和王建华继续争论的声音。
"哥哥,大姨夫好像不喜欢我们。"弟弟小声对我说。
"嘘,别说话。"我赶紧制止他,虽然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。
等了大概十分钟,大姨拿着袋子回来了。袋子看起来比之前重了一些,但也没有特别沉。
"好了,5斤面粉。"大姨把袋子递给我,脸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
我接过袋子,感觉确实比来的时候重了不少。
"谢谢大姨。"我真诚地说。
"不用谢,都是一家人。"大姨说,但语气听起来有些勉强。
这时候,王建华又从里屋出来了,看到我们准备走,他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。
"建国,回去告诉你爸爸,以后有什么困难,要早点想办法,不能总是临时抱佛脚。"他说,语气虽然缓和了,但话里还是带着教训的意味。
"我知道了,姨夫。"我点头应答。
"还有,这面粉你们拿回去好好吃,别浪费了。"他又补充道。
"不会浪费的。"我保证道。
大姨送我们到门口:"建国,路上小心点,雪这么大,慢点走。"
"大姨,您放心吧。"我背起袋子,牵着弟弟的手。
"大姨,再见!"弟弟礼貌地挥手告别。
"再见。"大姨挥挥手,然后就关上了门。
我们走在县城的街道上,我背着袋子,感觉比来的时候重了一些,但也没有重得离谱。
"哥哥,大姨家的人不太喜欢我们,对吗?"弟弟问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确实,从大姨夫的态度和大姨的为难表情来看,他们对我们的到来并不欢迎。
"可能是我们来得不是时候。"我找了个借口。
"那我们下次不来了吗?"弟弟又问。
"看情况吧。"我说。
其实我心里清楚,我们可能很难再有机会来大姨家了。今天这一趟,已经让双方都很尴尬。
05
回家的路更加艰难,雪越下越大,路面已经积了很厚的雪。我背着袋子,牵着弟弟,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
"哥哥,袋子重吗?"弟弟关心地问。
"还好,不太重。"我说。其实袋子确实有些重,但还在我能承受的范围内。
走了一个小时,弟弟又开始喊累。我蹲下身子让他趴在我背上,然后把袋子拎在手里。这样更累,但我不能让弟弟受苦。
"哥哥,你休息一下吧。"弟弟体贴地说。
"没事,我们快到家了。"我安慰他。
其实离家还有很远的路,但我不想让弟弟担心。
在路上,我一直在想今天在大姨家的经历。
虽然最终大姨还是给了我们面粉,但整个过程让我感觉很不舒服。
我能理解大姨夫的想法,毕竟他们的生活也不容易,但作为亲戚,这样的态度还是让人心寒。
"哥哥,我们家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呀?"弟弟在我背上问。
"很快的,等我长大了,就能赚钱让爸爸和你过好日子。"我坚定地说。
"我也要努力,我要和哥哥一起让爸爸过好日子。"弟弟认真地说。
听到弟弟的话,我心里暖暖的。虽然我们现在很困难,但至少我们一家人相互关爱,这比什么都重要。
天快黑的时候,我们终于到家了。远远地就看到我们家的烟囱冒着烟,父亲应该在等我们回来。
"爸爸!我们回来啦!"弟弟一看到家就兴奋地喊。
父亲听到声音,赶紧从屋里跑出来。看到我们平安回来,他脸上露出了放心的笑容。
"怎么这么晚才回来?我都担心死了。"父亲接过弟弟,上下打量着我们。
路上雪大,走得慢。"我解释。
"你大姨她...借给你们了吗?"父亲有些忐忑地问,眼神中带着期待和不安。
"借给了,爸,给您。"我把袋子递给父亲。
父亲接过袋子,掂了掂,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:"怎么这么重?不是说5斤面粉吗?"
我也觉得袋子似乎比5斤面粉要重一些,但当时也没有多想,以为可能是面粉比较密实。
"大姨说装了5斤面粉。"我如实回答。
父亲拎着袋子进了屋,我和弟弟跟在后面。屋里的炕烧得很热,让冻了一路的我们感觉很温暖。
父亲把袋子放在桌子上,看着我们说:"你们累了一天了,先休息一下,爸给你们热点水。"
"爸,大姨家的情况怎么样?"父亲一边忙活一边问。
我犹豫了一下,不知道该不该告诉父亲大姨夫的态度。
"还...还好。"我简单地回答。
"你大姨夫对你们怎么样?"父亲又问。
"也还行。"我不想让父亲难过,所以撒了个善意的谎言。
父亲点点头,似乎松了一口气:"那就好,毕竟是麻烦人家了。"
喝了热水,吃了一点剩饭,我和弟弟都感觉好多了。父亲看我们恢复了精神,才开始查看那袋面粉。
父亲小心翼翼地打开布袋,先看到的是白花花的面粉。
"这面粉真白,看起来是好面粉。"父亲说着,用手轻轻拨了拨面粉。
但当他的手触碰到面粉深处时,突然停住了,整个人瞬间愣在那里。
"这...这下面还有东西?"父亲的声音开始颤抖。
我好奇地探过头去看,只见父亲的手停在面粉里,表情变得非常震惊,但我看不清楚面粉下面到底是什么。
父亲颤抖着手慢慢拨开更多面粉,随着那些白色粉末被移开,一些其他的东西逐渐露出了轮廓。
当父亲看清楚那些东西时,他整个人瞬间瘫坐在炕沿上。
"这...这怎么能要..."父亲的眼泪"哗"地一下就流了出来,泣不成声...
06
父亲坐在那里哭了很久,手里还拿着袋子,但我们都看不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激动。
"爸,您怎么哭了?"弟弟被吓到了,怯生生地问。
我也很困惑,大姨明明只是给了我们5斤面粉,为什么父亲会有这样的反应?
父亲抹了抹眼泪,但怎么也止不住。他慢慢把袋子里的东西全部取出来,我这才看清楚:面粉下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叠钞票,还有几个小纸包,以及一张折叠着的纸条。
"爸,您怎么哭了?"弟弟被吓到了,怯生生地问。
我也震惊了。那一叠钞票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醒目,我粗略数了一下,至少有几十张。
父亲抹了抹眼泪,但怎么也止不住:"建国,这些钱...你大姨怎么能给这么多钱?"
我也被震惊了。一叠钞票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概念?父亲辛苦干一年农活,除去生活开销,能攒下的钱也就是这个数。
"爸,我真不知道大姨放了这些东西。"我诚实地说,"她只说装了5斤面粉。"
父亲又拿起那几个小纸包,打开一看,里面是一些药材,看起来很珍贵。
父亲不识字,把那张纸条递给我:"建国,你念念这上面写的什么。"
我接过纸条,展开一看,上面是大姨娟秀的字迹:
"大山哥,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好,咳嗽得厉害,这些药是我托人从省城买的,专门治肺病的。钱你不要推辞,孩子们正在长身体,不能饿着。建华不懂事,说话冲,你别往心里去。我们是一家人,有困难就要互相帮助。秀华留。"
我念完,父亲的眼泪流得更凶了。
你...你跟你大姨说我咳嗽的事了?"父亲看着我。
我想了想,摇摇头:"我没说,我只说您身体还行。"
"那她怎么知道我咳嗽?"父亲疑惑地问。
我也想不明白,但现在这些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大姨在明知道她丈夫不愿意的情况下,还是偷偷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。
父亲仔细数了数那些钞票,总共一百二十块钱。再加上那些珍贵的药材,这份礼太重了。
"建国,这些钱我们不能要。"父亲坚决地说,"明天你就送回去。"
"爸,大姨既然给了,就是想帮助我们。"我劝道。
"帮助是帮助,但这太多了。"父亲摇头,"一百二十块钱,够我们家用大半年的。我们不能要这么多。"
我理解父亲的想法,他是个有骨气的人,不愿意接受太多的帮助。但我也知道,我们家现在确实需要这些钱。
"爸,您的咳嗽越来越严重了,应该去看医生。"我说。
"咳嗽不是什么大病,过几天就好了。"父亲推脱。
"爸,大姨都给您买药了,说明她也觉得您应该看病。"我继续劝说。
父亲看着那些药材,陷入了沉思。
那天晚上,父亲用大姨给的面粉给我们煮了一锅热腾腾的面条,还打了两个鸡蛋。这是我们很久以来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。
吃饭的时候,父亲一直很沉默,偶尔看看我和弟弟,眼中满是复杂的情感。
"爸,面条真香。"弟弟吃得很香,小嘴巴上沾着汤汁。
"嗯,多吃点,把身体养好。"父亲勉强笑了笑。
吃完饭,父亲把我叫到一边:
"建国,今天在你大姨家,真的没有别的事吗?"
我犹豫了一下,最终还是决定告诉父亲实情:"爸,大姨夫不太愿意借给我们面粉,他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。但大姨还是给了我们。"
父亲的脸色变了:"他说什么了?"
"他说...他说现在经常有人来借东西,不能开先例。"我小心地说。
父亲长叹一口气:"是我让你们为难了。"
"爸,没关系,最终大姨还是帮助了我们。"我安慰父亲。
"但是这样一来,你大姨在家里会不好过。"父亲担心地说,"她丈夫本来就不愿意,她偷偷给我们这么多东西,回头被发现了怎么办?"
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。王建华本来就不愿意帮助我们,如果他知道大姨私下给了我们这么多钱和药材,肯定会很生气。
"爸,那我们该怎么办?"我问。
父亲想了想,说:"明天我亲自去一趟,把钱还给你大姨,只留下药材和面粉。"
"可是您咳嗽这么厉害,不应该去县里。"我担心地说。
"没事,这事我必须处理好。"父亲坚持道。
07
第二天一早,父亲就开始准备去县里。虽然他的咳嗽依然很严重,但他执意要去。
"爸,要不我和您一起去?"我提议。
"不用,你在家照顾建军。"父亲摇头,"这是大人之间的事,我自己去处理。"
父亲把那一百二十块钱重新包好,装在怀里,然后踏着雪去了县城。
我在家里等了一整天,心里忐忑不安。不知道父亲和大姨会聊些什么,也不知道王建华会是什么反应。
傍晚时分,父亲终于回来了。我看到他脸色很苍白,但眼神中有一种释然的感觉。
"爸,怎么样?"我急切地问。
父亲坐下来,长出一口气:"你大姨是个好人,真的是个好人。"
"她愿意收回钱了吗?"我问。
"开始不愿意,后来在我的坚持下,她收回了一半,留了六十块钱给我们。"父亲说,"她说这些钱是给你们上学用的,无论如何不能再还回去。"
我松了一口气,这样的结果对双方都比较合适。
"大姨夫知道这事吗?"我又问。
"知道了。"父亲点头,"你大姨把情况都告诉他了,包括她偷偷给我们钱的事。"
"他生气了吗?"
"开始有些生气,但听你大姨解释了我们家的情况后,他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。"父亲说,"他让我以后有困难不要硬撑着,但也不要动不动就找他们。"
我理解王建华的想法,他不是坏人,只是不想被人当成提款机。
"爸,那些药材呢?"我问。
"留下了,你大姨坚持要我用。"父亲说,"她还给我写了用法,说这些药对我的咳嗽很有用。"
当天晚上,父亲就开始按照大姨的方法服用那些药材。虽然味道很苦,但他坚持每天都喝。
几天后,我发现父亲的咳嗽确实有所好转,夜里咳嗽的次数明显减少了。
有了这六十块钱,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。父亲不再为每天的吃饭问题发愁,还给我和弟弟各买了一套新衣服。
更重要的是,父亲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问题。一个月后,他用这些钱去县医院做了检查,医生说是慢性支气管炎,需要好好调养。
有了明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,父亲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。再加上大姨给的那些药材,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。
08
春天来临的时候,父亲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了。他开始重新投入到农活中,准备新一年的耕种。
"建国,今年我们要好好种地,争取有个好收成。"父亲信心满满地说。
"嗯,我和建军也会帮忙的。"我点头回应。
这一年的收成确实不错,秋天的时候,我们家的玉米产量比往年高了很多。父亲把多余的粮食卖掉,不仅还清了之前的一些欠账,还攒下了一笔钱。
"建国,明年你就要考初中了,爸爸要给你准备学费。"父亲高兴地说。
我点点头,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
年底的时候,父亲决定去大姨家拜年,感谢她的帮助。
"这次我们全家一起去,好好谢谢你大姨。"父亲说。
我们准备了一些土特产,还有父亲亲手做的腊肉,一家三口一起去了县城。
到了大姨家,这次的接待明显比上次热情多了。大姨看到我们来,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。
"大山哥,你的气色好多了!"大姨高兴地说。
"多亏了你给的药,现在已经完全好了。"父亲感激地说。
王建华也出来迎接我们,虽然还是不太爱说话,但态度比上次友善了许多。
"建国长高了不少。"他看着我说,"学习怎么样?"
"还可以,经常考第一名。"我有些自豪地回答。
"好,要继续努力,将来考个好学校。"王建华鼓励道。
这次我们在大姨家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,一家人其乐融融,没有了去年的尴尬和紧张。
临走的时候,大姨又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年货,但这次父亲没有推辞,因为我们也带来了自己家的土特产作为回礼。
"大山哥,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,我们是一家人。"大姨真诚地说。
"谢谢你,秀华,真的谢谢你。"父亲眼中含着泪水。
回家的路上,父亲对我和弟弟说:"记住大姨的恩情,将来有能力了,一定要报答她。"
"我们会的,爸。"我和弟弟齐声回答。
09
接下来的几年,我们家的生活越来越好。我顺利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中,弟弟也开始上小学了。
父亲的身体完全康复后,除了种地,还开始做一些小生意,日子过得越来越有起色。
我在学校里表现优异,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。每当有人问起我为什么这么努力学习时,我总会想起那个雪夜,想起大姨的恩情,想起父亲流下的眼泪。
三年后,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高中。这个消息传到大姨家,她比我们还要高兴。
"建国真是争气!"大姨在电话里激动地说,"大山哥,你有个好儿子!"
高中三年,我更加刻苦学习。我知道,只有通过知识改变命运,才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,才能报答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。
高考的时候,我发挥出色,被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录取。
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,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,他立刻给大姨打电话报喜。
"秀华,建国考上北京的大学了!"父亲在电话里激动地说。
"太好了!我就知道这孩子有出息!"大姨的声音里也充满了喜悦。
大学四年,我学习努力,品学兼优。毕业后,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,月薪比父亲一年的收入还要高。
工作稳定后,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亲和弟弟接到北京来生活。
"爸,以后您就不用再种地了,安心享福吧。"我说。
"建国,你真是爸爸的骄傲。"父亲眼中含着泪水,"你妈妈要是还在,看到你这样出息,该多高兴啊。"
10
弟弟也很争气,后来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,学的是医学专业。毕业后,他回到老家的县医院工作,立志要帮助更多像我们家当年那样的困难家庭。
我在北京站稳脚跟后,经常回老家看望大姨。每次去,我都会带上一些礼物,表达我们全家的感激之情。
"大姨,如果没有您当年的帮助,就没有我们家今天的生活。"我真诚地说。
"傻孩子,一家人说什么感谢的话。"大姨笑着说,"看到你们过得好,我比什么都高兴。"
王建华也老了许多,但对我们的态度完全变了。他经常夸我有出息,说当年的投资是值得的。
"建国,你是我们家的骄傲。"他说,"当年你大姨坚持要帮助你们,现在看来她的眼光是对的。"
我明白,王建华当年的态度并没有错,他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家庭。但大姨的慷慨和善良,确实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。
现在,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。每当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,我总会告诉他那个雪夜的故事,告诉他大姨的恩情。
"记住,孩子,血浓于水的亲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。"我对儿子说,"那些在你困难时伸出援手的人,值得你用一生去感恩。"
儿子认真地点点头:"爸爸,我记住了。"
每年过年,我都会回老家,给大姨拜年。
虽然她现在头发已经花白,但在我心中,她永远是那个在我们最困难时伸出援手的女人。
有时候我会想,如果当年大姨没有偷偷给我们那些钱和药材,我们家会是什么样子?
父亲的病会不会更严重?我还能不能继续上学?
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,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,而那份恩情,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
如今,我已经四十多岁了,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。
但每当看到那个当年装面粉的布袋子(我一直保存着),我都会想起1987年那个寒冷的冬天,想起大姨的恩情,想起父亲流下的那些眼泪。
那些眼泪,不仅仅是因为感动,更是因为在最困难的时候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。
现在,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,身体依然硬朗。弟弟也成为了县医院的业务骨干,娶妻生子,过着幸福的生活。
大姨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,但身体还算硬朗。每年我们全家都会去看她,感谢她当年的恩情。
这就是我想要告诉所有人的故事:在这个世界上,血浓于水的亲情永远是最珍贵的财富。
那些在你困难时伸出援手的人,即使他们的帮助看起来微不足道,但对于受助者来说,却可能改变整个人生的轨迹。
真正的善良,不是高调的慈善,而是在别人需要时,默默伸出的援手。
大姨就是这样的人,她的善良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,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血浓于水的亲情。
发布于:河南省股票杠杆炒股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